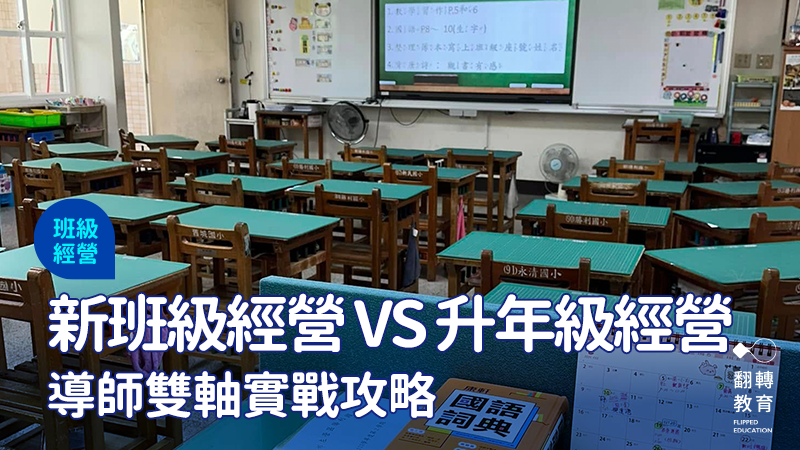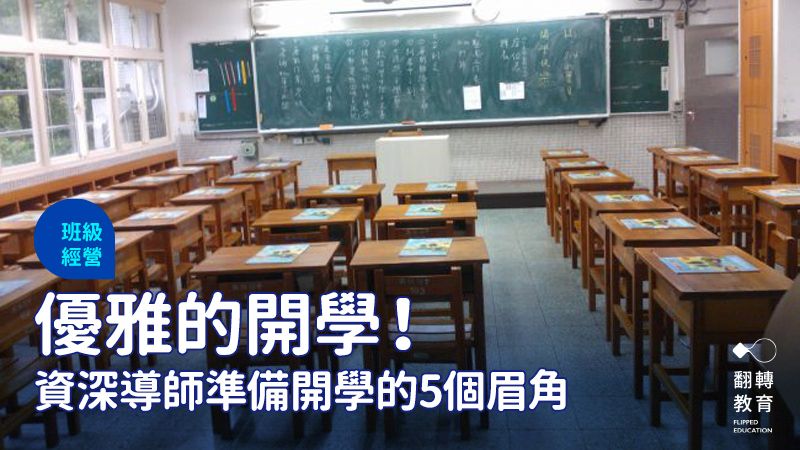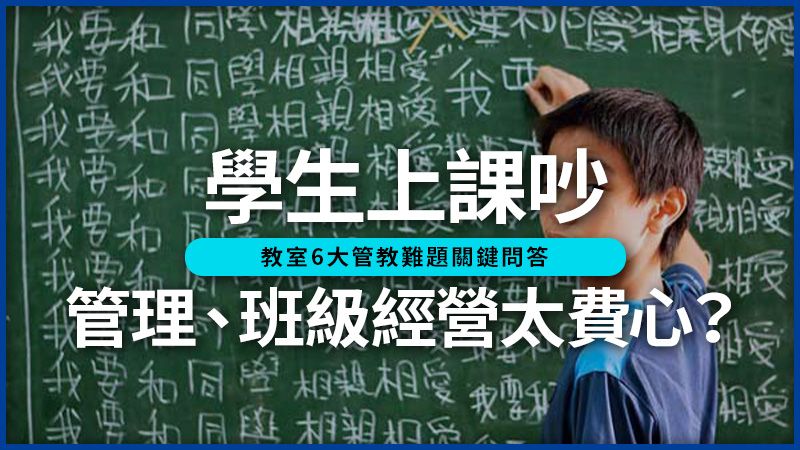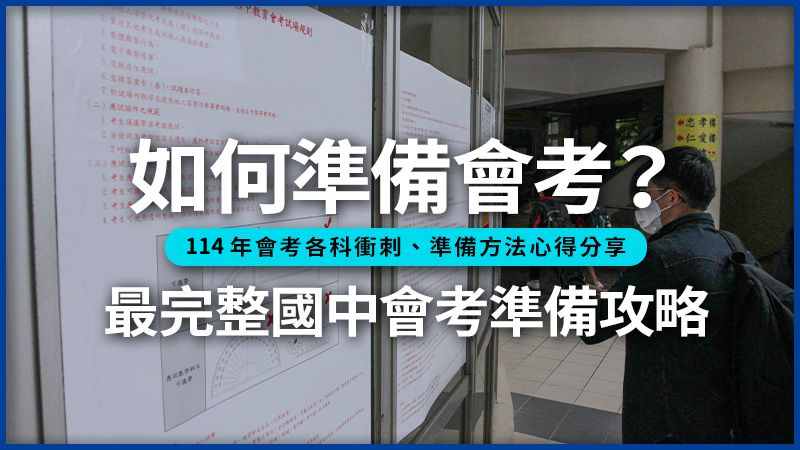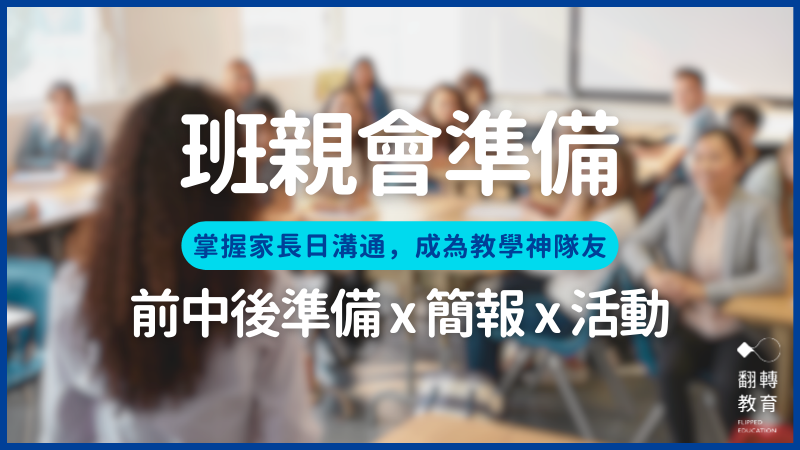新生訓練裡的導師生存錄:老師也需要SEL
國中教師晶瑩老師分享班導在新生訓練的現場感受極限壓力,在時間與制度夾縫中,重新摸索如何陪伴學生,也反思導師角色在教育制度中的位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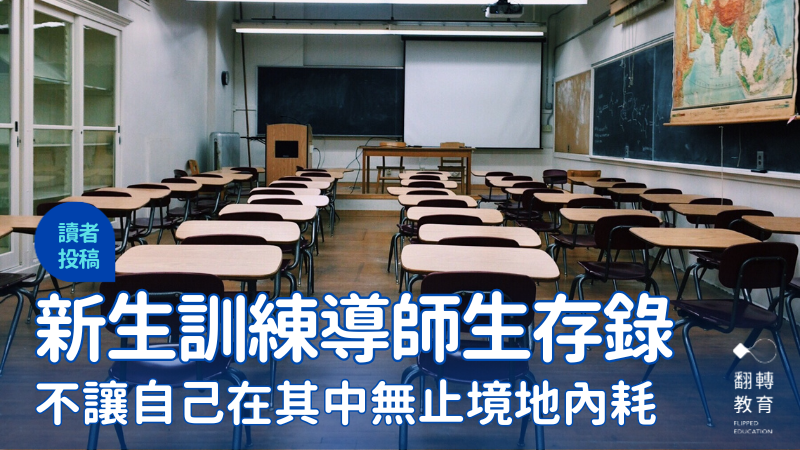
在孤島與洪流之間:新生訓練裡的導師生存錄。圖片來源:WOKANDAPIX (pixabay)
有人說,教師轉場像換了一片土壤:有時鬆軟肥沃,有時乾裂貧瘠。而我,在這場新生訓練中,成了那株被迫重新扎根的老樹。
過去,我曾在一所流程周延、分工清晰的邊陲學校任教。行政像五星級服務團隊:回條整合、提醒精準、可溝通微調、時程寬裕,導師得以安心陪伴學生。然而今年,剛轉入大型校區的我,在新生訓練第一天,迎來的卻是另一種「行政高度」──天花板式的交辦文化。所有流程與事項都「快速交付、立即回收」,而落實與執行的細節,全數落在導師肩上。從來沒想過,長達一天半的新訓,竟然能如此徹底測試一位導師的抗壓指數。
教育哲學家杜威(John Dewey)曾說:「學校不只是為了傳授知識,而是生活本身。」但在現場,我所經歷的,不是生活的滋養,而是一場極限壓力測驗:在制度與時間的夾縫中,教師如何讓一個班級「活起來」,還不至於讓自己「垮下去」。
一、1.5 天的極限挑戰:新生訓練現場實錄
新訓首日,我站在教室黑板前,一邊書寫處室交辦事項,一邊感覺自己彷彿成了進行任務部署的中樞。健康卡、各式回條、制服領取、課本分發、午餐流程、掃地體驗⋯⋯密密麻麻地列下來,竟然足足有十三條之多。黑板成了壓力牆,每一筆都是一道倒數的時鐘。
最艱難的一刻,是那場「搬運」。八個新生在學長姐的帶領下,肩挑手提著沉重的制服與紙箱,步伐緩慢,像一場沒有終點的行軍。接著,一箱又一箱厚重的課本,再度壓在孩子們瘦小的身軀上。看著他們走走停停,汗水不斷滲出,肩膀被重量壓得前傾,我終究也加入其中。
搬運的,不只是制服與課本的重量,更是制度默默轉嫁在導師與學生身上的負荷。
那一刻,我腦中浮現的不是教學專業的藍圖,而是一個悶在心底的疑問:「這樣的環節,曾有人認真推演過嗎?還是只要把任務交辦出去,就算完成?至於最後的重量,由誰來承擔,早已無人在意。」
緊接著午餐時段迫在眉睫,一群氣喘吁吁的學生還得再度下樓,遠征體驗班餐桶。幸好有資深在地老師的提醒,讓我得以在返校日提前安排學生擔任午餐志工,否則新生的第一餐恐怕會亂成一團。
午休時,我翻看下午流程表,卻發現其中沒有任何「發放課本、制服、帽子、書包與提袋」的時段,僅僅留下一句「導師時間:請安排掃地工作」。於是,我只好趁著學生午休,將一箱箱書打開,把課本一科一科整齊地擺在桌上,臨時規劃出一場「自助餐模式」的分發:學生分兩列依序取書,學長姊在旁逐一核對。
這場即興策劃的「書本饗宴」,沒有華麗的菜色,卻在半小時內讓每個孩子都領到自己的份。教育或許也是如此──重點從來不在於儀式的隆重與形式的完美,而在於是否能讓每個學生都「分得到、帶得走」。
下午的「掃地體驗」再度刷新了導師的極限。我們班被分配到操場邊,一片落葉堆積的廣大區域,既遙遠又勞累。新生們氣喘吁吁地揮掃,我只好一旁陪著,也親自示範如何掃落葉,並對那些邊掃邊抱怨、滿頭大汗的孩子說:「慢慢來,今天先學怎麼掃,改天再繼續。」而此時,教室裡的另一群新生正獨自進行清掃,我根本無暇兼顧,只能把最大信任交給衛生股長。
1.5 天看似短暫,卻濃縮了國一導師的百般壓力修練之旅。新生是在學習如何「適應」國中生活,而導師則像被投入急湍的洪流,不得不邊掙扎邊學會游泳;又像被孤立於一座荒島,只能調整心態,在有限資源裡尋找自我保存與求生的方式。
二、生存秘笈備忘錄:在各自為政的體系中找到呼吸縫隙
身為一位資深卻因轉場而再次摸索的導師,我深知:當行政流程如此簡化時,前線的老師只能臨機應變,在縫隙裡自尋出路。
這段經驗,讓我整理出五個小小的「生存秘笈」,獻給即將返校、準備迎戰新訓的同路人:
- 黑板場控術:將處室任務與時序逐一條列,讓師生都能一目了然,避免陷入手忙腳亂。
- 掃地抽籤制:用編號抽籤分配工作,簡單、公平又快速,爭執自然減少。
- 午餐志工透明化:把角色分工與動線圖清楚寫在黑板上,人人都明白自己該做什麼,效率倍增。
- 課本「自助餐模式」:事先將書本一科科擺好,學生分兩列排隊依序領取,幹部逐一核對,更迅速有效率。
- 預備學習單:當導師時間過長、學生開始躁動時,一份簡單的自我介紹或小小反思,既能安定氛圍,也讓彼此更快熟悉。
方法或許不完美,但正因不完美,才提醒我們:教育的核心,不在秩序的無瑕,而在師生同行的安然。縱使被碎片環伺,在陪伴學生的過程裡,仍能找到專業的重量與心的安定。
三、SEL提醒:在制度窠臼中安放自己
制度或許一時難以撼動,但我們仍能選擇──不讓自己在其中無止境地內耗。此刻,SEL(社會情緒學習)不只是寫在教材裡的框架,不只是教給學生的能力,它更像是導師自我安放的一本生存手冊:
- 自我覺察:允許自己感到疲累與無力。那不是專業的缺口,而是制度的冰冷,使人難以呼吸。
- 自我管理:提前規劃、隨時調整,並非為了追求效率,而是給自己一份溫柔的保護。
- 社會覺察:學會求助,也學會感謝。若非在地資深導師的提醒與支援,我早已陷落在崩盤邊緣。
- 關係技巧:把學生成為合作的夥伴。志工、幹部、流程與用意交代──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,其實正是信任的開始。
- 負責任的決策:對自己說「做到這裡就好」。這不是退讓,而是保留續航力,為了能走得更長遠。
SEL 提醒我們:教育的課題,從來不只是「如何教會學生」,更是「如何不在教的過程裡失去自己」。
結語
轉場,對教師而言,從來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改變;它更像是一場心靈的遷徙──教學信念、班級經營、與行政互動的方式,都必須重新調頻。
新生訓練,本該是孩子展開新篇章的序曲,卻常常成了導師的壓力測驗。崩潰,不只是初任新手的專利;即使是經驗豐富的老師,在陌生而冷漠的體制裡,也會再一次感受到「新生」的無措。
然而,我仍選擇相信:即便被拋入急湍的洪流,我們仍能學會游泳;即便暫時漂泊在孤島,我們仍能在有限資源中搭建庇護。我們不為名,但求心安;不求完美,但求初心不滅。
因為教育的靈魂,不在天花板的高度與厚度,而在一間教室裡、一雙雙眼神的交會──那是彼此看見的瞬間。
只要我們還記得:我們為誰而來,就能撐過風雨,繼續前行。

您可能有興趣